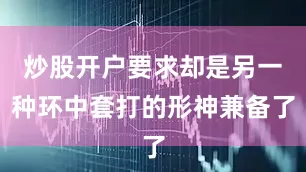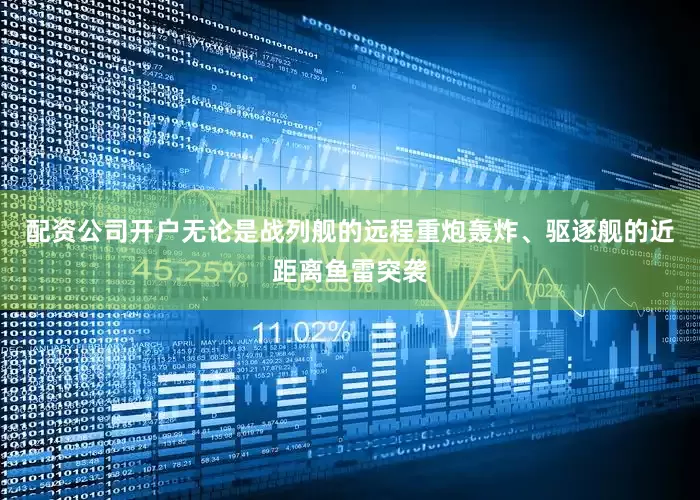手握兵权和钱袋子,为何黄兴甘心给孙中山当二把手?
说起清末那段风云激荡的日子,咱们聊孙中山聊得多,可他身边那位猛人——黄兴,却常常被一笔带过。这事儿就有意思了,要是把革命比作开公司,孙中山是董事长,负责画大饼、定方向,那黄兴妥妥的就是手握实权的CEO加武装部长,钱、人、枪,几乎都在他手里。可怪就怪在,这位“CEO”一辈子都没想过把董事长给掀了,反倒是处处维护,你说奇不奇?
这根子,得从他小时候说起。黄兴,湖南长沙人,家里是地主,从小念的是《四书五经》,22岁就考上了秀才。你别小看这个秀才身份,这在当时就等于拿到了“士大夫”阶层的入场券。骨子里,他被刻上了一套行为准则,那就是“辅佐明君,经世致用”。说白了,他的人生理想天花板,是当萧何、当张良,而不是自己去当刘邦。自己坐龙椅,那念头,在他的知识体系里压根就不存在,那是“僭越”。

这套思想,就像电脑的底层代码,决定了他日后所有的人生选择。
1903年,黄兴从日本留学回来,一腔热血,在湖南老家拉起了一支队伍,叫华兴会。他自己当会长,还把当地的江湖组织“哥老会”上万人给收编了,甚至变卖家产来筹集军费。那架势,是要在湖南干一票大的。可惜,两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。这两盆冷水,直接把他给浇醒了。他可能意识到,自己或许是个优秀的战将,但未必是个能一呼百应的领袖。那种“天命所归”的气场,他身上好像缺了点。

这时候,他遇到了孙中山。1905年,两人在日本见面,一拍即合,决定把黄兴的华兴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,成立同盟会。成立大会上,到场的八十多号人里,有七十个是跟着黄兴混的。按理说,这会长宝座,黄兴坐上去天经地义。可他倒好,直接站起来说:“孙先生是咱们的总理,这事不用选了。”就把孙中山稳稳地推了上去,自己呢,跑去当了个“执行部庶务”,干起了处理日常杂务的活儿。
他还把九十多个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会员证都攥在自己手里,成立了一个叫“丈夫团”的组织。这可不是什么仪仗队,而是敢死队,是同盟会最精锐的军事力量。枪杆子,牢牢握在他黄兴手里。

同盟会内部,那叫一个山头林立,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闹。好几次,都有人想把孙中山这个“董事长”给换掉。1907年,章太炎因为经费问题跟孙中山闹掰了,公开喊话要罢免孙中山,改选黄兴。黄兴听了,就回了一句话:“革命是搞事业,不是争位置。”硬是把这股歪风给压了下去。
没过多久,又有人另立山头,搞出个“共进会”,眼看同盟会就要分裂。黄兴急得直拍桌子,对着那帮人吼:“革命搞出两个中心,将来听谁的?”逼着双方都退了一步,才没让这刚成立的公司散伙。最悬的一次是1909年,陶成章写了洋洋洒洒一篇《孙文罪状》,到处散发,搞得人心惶惶。黄兴二话不说,亲自跑到南洋去灭火,一边安抚同志,一边给孙中山写信打气:“你放心,这些闲言碎语,我拼了命也会给你挡住。”

你品品,那时候他手里有枪、有人、有威望,只要他稍微点个头,孙中山的位置立马就得换人。可他偏不,他选择当那个默默守护的“金刚”。
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,天下响应。各省代表齐聚南京,商量着成立临时政府,要选个大元帅。投票结果一出来,黎元洪第一,黄兴第二,当了副元帅。当时黎元洪还在武昌,南京这边的军政大权,实际上全在黄兴这位副元帅手里。不少代表私底下都把他看作是未来的第一任大总统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消息传来:“孙中山先生已经在回国的船上了。”黄兴听到这话,当天就把副元帅的委任状锁进了抽屉。他对身边的人说:“孙先生是咱们同盟会的总理,我要是抢先坐了这个位置,他心里肯定不舒服。党内一旦有了猜忌,这革命的果子就算白摘了。”
他还特意翻出太平天国的档案给大伙儿看,痛心疾首地说,当年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内斗,是怎么把大好江山给葬送的。咱们不能重蹈覆覆辙,要学萧何,别学韩信。最后,在选举临时大总统的会议上,黄兴带头把票投给了孙中山,自己连个提名都没要。

当然,黄兴也不是没脾气的泥人。在决定民国国旗样式的时候,他就跟孙中山结结实实地干了一架。
孙中山坚持要用兴中会的“青天白日旗”,说这是革命的象征。黄兴却拿出了自己设计的“井字旗”,中间一个“井”字,他说这代表了同盟会“平均地权”的纲领,让耕者有其田。两个人在总统府办公室里,从下午吵到天黑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黄兴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,说当年华兴会起义,十万兄弟认的就是这个旗,现在换旗就是忘本!孙中山也拍了桌子,说青天白日旗是七十二烈士的鲜血染红的,不能换!
黄兴气得两天没上班,把自己关在参谋本部,谁也不见。他觉得,这不单单是旗子好不好看的问题,这关系到革命的根本承诺能不能兑现。不过,最终他还是妥协了。据说,他把井字旗的图样锁进抽屉时,长叹一声,说了句:“功劳不必由我来立,名声不必由我来成。为了大局,我只能听先生的了。”他后来跟人解释,他争的不是一面旗,是怕“平均地权”最后成了一句空话。但一个团体不能有两个声音,先生的权威必须维护,总得有个人退一步。有趣的是,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并非孙中山的完胜,临时参议院最后通过的是“五色旗”作为国旗,代表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共和,这恰恰体现了当时各派势力妥协的结果。
黄兴就是这样一个人,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,但在大是大非面前,他总能把个人的荣辱得失放在一边。他戎马一生,亲自参与了无数次起义,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,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被子弹打断,人称“八指将军”。这样一个在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铁血汉子,却甘愿在一个精神领袖身后,默默地扛起所有最苦最累的活。
说到底,黄兴的选择,是他骨子里那套“士大夫”精神的体现。他把自己定位为革命的执行者、守护者,而不是开创者。他觉得自己的历史使命,就是辅佐孙中山这位“天选之人”完成大业。这种近乎于“愚忠”的品质,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,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,恰恰是这种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牺牲精神,才让无数看似不可能的理想,最终照进了现实。他的“退”,恰恰成就了革命的“进”。
华亿配资-公司配资炒股-配资平台安全查询官网-配资中国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